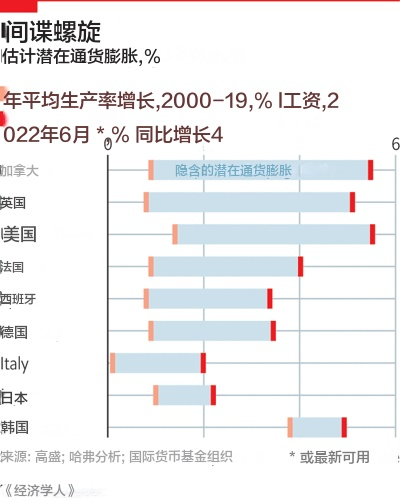Who Saw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Coming?
在苏联解体30周年之际,我们询问了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分析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及它对俄罗斯的未来有什么启示。

摄影: 塔斯社/塔斯社
作者
Clara Ferreira Marques

1991年12月25日,由于无法克服几个月前强硬政变和苏维埃共和国独立运动带来的打击,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辞职。最后一位苏联领导人希望改革共产主义,而不是取代它,但他无法遏制自己的改革释放出的离心力。疾病缠身、四分五裂的苏联走到了尽头。
“旧的系统在新的系统开始工作之前就崩溃了,”他在他的报告中说 传唤要求俄罗斯维护来之不易的民主自由。在俄罗斯执政期间,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转而恢复了一个一直延续至今的个人权力体系
我们询问了一些研究俄罗斯和苏联的顶尖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观察家,为什么这场崩溃会让如此多的人感到意外,以及如今克里姆林宫的占领者——以及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总统领导下的俄罗斯的学生——应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
谢尔盖•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是一位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威尔逊•施密特(Wilson E. Schmidt)杰出教授。
之所以很少有人预测到苏联的解体,是因为从表面上看,苏联似乎是一个拥有广泛安全机构的强大兵权。很少有观察家能够理解这个体制的合法性有多少,腐败的腐败、对意识形态的失去信心、令人沮丧的生活水平,以及最后一点,精英们的内斗,从内部蚕食了这个体制。最终是精英阶层的叛逃导致了它的垮台——这一点,以及它缺乏整体合法性。苏联的目的是什么,看到建设共产主义不再是可能的?
普京利用了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这是一股远比苏联所吹嘘的更强大的民族团结力量。因此,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天生更加稳定。然而,俄罗斯也面临着一些与前苏联相同的问题,包括合法性不足(在缺乏自由和公正选举的情况下)、前苏联前所未见的腐败规模、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以及随着普京年龄的增长,精英内斗。因此,尽管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分裂成准独立的公国,但该国已经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唯一的问题是在另一端等待着什么,以及过渡时期会有多么激烈。
怀旧陷阱
当被问及是否对苏联解体感到遗憾时,俄罗斯人是最怀念这个帝国的前公民之一
资料来源: 勒瓦达中心,2020年
注: 2020年2月,俄罗斯受访者被问及“你对苏联解体感到遗憾吗?”。
谢尔盖•古里耶夫(Sergei Guriev)是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 Paris)经济学教授。2013年之前,他一直担任莫斯科新经济学院(New Economic School)院长。
大多数人无法预测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会分崩离析,这很正常。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然而,有迹象表明。如果有些事情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它就会停止——这是(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1986年提出的定律,与苏联无关。苏联经济无法带来生产力增长。为了提供稳定的生活水平,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借钱。由于体制僵化,苏联无法进行改革。最终,市场看到苏联无法偿还债务。
在最近的时期,你可以参考次贷危机(尽管一些人和一些学术经济学家确实预测到了)和希腊危机(结果发现,希腊债务的很大一部分被隐藏了起来)。没有人预料到欧元区会出现违约。
普京吸取了很多教训。首先,俄罗斯的宏观经济政策要保守得多,通胀得到控制,拥有大量外汇储备,预算平衡,没有外债。其次,尽管俄罗斯由政府主导,价格守则也是临时性的,但它仍然是一个市场经济,而且比苏联更有效率,也更有弹性。
然而,世界应该记住,随着苏联政权的垮台,俄罗斯也可以。苏联政权是意识形态和学院派的,普京则是个人主义的。正如议会发言人维亚切斯拉夫(Vyacheslav)所言: “没有普京,就没有俄罗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政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Post-Putin Russia 的情况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但肯定会有所不同。

摄影: TV GRAB/AFP via Getty Images
叶甫盖尼亚 · 阿尔巴茨是《新时代》的调查记者和编辑。她也是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颇为引人注目的是,”红旗落地”冰没有被苏联学家、情报专家和政治学家的集团所预测。
在我看来,这种失败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缺乏在实地收集到的真实生活信息,而不是在阅兵式期间观察共产党高层在列宁陵墓主席台上的变化。
第二个原因与学术分析的过度政治化有关。例如,罗纳德 · 里根著名的“邪恶帝国”,他称之为苏联(苏联内部的异见人士非常欣赏这一点) ,这导致了所谓的太空战争——逐步升级的军备竞赛——被许多学术界认为是鹰派,我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发现了这一点。然而,这种鹰派政策在苏联过度军事化经济的棺材上钉上了一颗相当重要的钉子,并导致了政权的崩溃。
最后,第三个也是最致命的原因,因为它的长期影响,是以牺牲制度为代价的过度个人化的政治实践。关于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机构,这是事实。同样的道理,现任俄罗斯领导人、过去20多年的独裁者弗拉基米尔 · 普京(Vladimir Putin)也是如此。在该领域的许多专家看来,普京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且比他经常喝醉的前任鲍里斯 · 叶利钦(Boris Yeltsin)更加得到认可。因此,几乎没有人(20年前)预见到这样的危险: 普京是苏联最专制、最强大的机构——克格勃(KGB)的代表。如果有人提出这种担忧,说一个基于残酷武力而非法律规则的机构接管了俄罗斯,通常的回应(直到2014年併吞克里米亚敲响了警钟)是: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是中央情报局(CIA)局长。
在对俄罗斯发展的分析中,克格勃从被遗忘的状态中凯旋而归被大大忽视和低估了。后果就发生在乌克兰边境,10多万俄罗斯军队即将入侵邻国。
新模范军队
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计划推高了军事经费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例
来源: 世行,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erhii Plokhy 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和该校乌克兰研究所所长。他是《最后的帝国: 苏联最后的日子》一书的作者
华盛顿和欧洲各国首都的政策制定者、记者和广大公众首先知道苏联是俄罗斯——如果不是一个欧洲式的民族国家,那么就是一个拥有共和国而不是美国式国家的美国。在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对英国这样的老式帝国怀有共同的敌意,并争取到了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成为独立国家的前帝国殖民地。但是苏联,或者说“俄罗斯”,在国内并不被认为是一个帝国,因为它的统治者声称通过在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创造一个统一的“苏维埃人民”,解决了1917年前俄罗斯帝国的民族问题。
因此,1991年苏联帝国灭亡,沿着15个共和国的民族边界解体,这对西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苏联内部其他有抱负的国家,如车臣,也未能成功地走出帝国的子宫。西方苏维埃学可能预测到了这样的结果,但它几乎没有关注苏联的多民族组成,而是关注克里姆林宫政治、俄罗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的军事能力。很少有专家意识到,俄罗斯人只占克里姆林宫宣传人员所说的“苏联人民”的一半多一点(确切地说是50.8%) ,更不用说整个西方公众了。
根据上一次人口普查,俄罗斯人约占后苏联俄罗斯人口的81% 。如今有多少政客和外交官考虑到了这一点,又有多少公众知道,如今几乎五分之一的“俄罗斯人”根本不是俄罗斯族人?最多也就几个。在许多情况下,非俄罗斯人生活在祖传的领土上,这些领土在沙皇时代被圣彼得堡或莫斯科吞并,当时是多民族的俄罗斯帝国。鉴于西方对非俄罗斯人的这种盲点,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认为自己在“俄罗斯”中是平等的,未来我们将面临更令人震惊的政治发展。
回到苏联
1990年3月,立陶宛成为第一个脱离联邦的共和国。一年多后,苏联解体,给予物成为15个独立国家

塔蒂亚娜•斯塔诺瓦亚(Tatiana Stanovaya)是政治分析公司 R. Politik 的创始人和行政长官,也是卡内基莫斯科中心(Carnegie Moscow Center)的非常驻学者。
对普京个人而言,至少有三个与苏联有关的敏感问题具有巨大的情感意义,而且在寻求理解普京动机时,世界应该考虑到这些问题。首先,他认为俄罗斯必须是一个单一国,苏联暗示民族自治的经验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普京曾多次被告列宁“在俄罗斯的国家地位之下放置了一枚具有象征意义的炸弹,向不同民族提供自己的领土和脱离俄罗斯的权利”,“摧毁了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国家”——普京认为他可以恢复和执行这一点。这表明,普京有多么不喜欢与一个联邦化的俄罗斯打交道,他更愿意处理统治这个单一单位的国家。这也显示出普京对地区野心的强烈恐惧。
其次,普京多年来一直在制造对国家的狂热崇拜,这意味着国家作为一个机构,无条件地优先于任何其他社会或私人利益,并从长远的国家利益出发行事。这就是为什么他寻求,例如,恢复斯大林的统治——尽管他个人谴责政治镇压和大规模恐怖主义,但他相信,在某些关键情况下,国家可能拥有“紧急”权力,如果“国家利益”要求,国家可能会采取远远超出法律范围的行动。相信国家有权采取非常行动,使他在道义上和历史上有理由采取可能越过其他世界参与者红线的行动。然而,他也认为,各国必须在相互依存和保证多边互不侵犯的原则下,就共同规则达成一致。
第三,普京认为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认为,国家必须受到保护,不受“政治”批评,因为这些批评会使国家在敌对环境中变得更弱、更脆弱。由于普京认为如今的俄罗斯在永久的地缘政治威胁下是一个被围困的堡垒,他将严厉镇压任何真正的反对派——因为他认为反对派是反国家的,而不是反对他自己的政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政治话语的回归会赞扬一些苏联的做法,比如少先队、 Komsomol、爱国主义教育等等。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可能滑入日常生活的苏维埃化,但它肯定会进一步摆脱民主程序,更快地走向强制性的政治和社会巩固,而不是走向政治多样性和公开讨论。

摄影: Anatoly Kuzyarin/TASS via Getty Images
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Zubok)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国际史教授。他的最新著作是《崩溃: 苏联的解体》
观察家和历史学家解释1991年苏联的突然崩溃是由长期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如计划经济破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效、冷战压力以及边境地区民族主义者的叛乱。正如我在书中所解释的那样,这种崩溃是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选择造成的,最主要的是设计极其拙劣的经济改革和快速的政治自由化。他们制造了一场完美的风暴吞噬了苏联船只和倒霉的船长。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毁掉了卢布,使中央政府失去了资金。他的政治宪法改革在整个苏联引发了叛乱。俄罗斯退欧最致命的现象——俄罗斯人的分离主义,他们的不满导致了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成为俄罗斯领导人。俄国人摧毁了许多人认为属于他们自己的“帝国”和中央政府。苏联是被中心的内爆杀死的,而不是被外围的压力杀死的。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从这个故事中汲取了重要教训。他誓言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并积累了巨额财政储备,以此作为安全措施。即使在大流行的时候,他也不愿意打开他的金库。在石油价格的帮助下,他投入了巨大的资源来恢复国家权力、军队、警察和对暴力的垄断。
然而,普京正在努力吸取一个教训。苏联是一个邦联,当其核心俄罗斯宣称独立和主权时,它就不可挽回地解体了。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这个联盟身上吗?俄罗斯宪法现在是一条单行道: 联邦主体没有出路,包括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和被征服的车臣。但风险依然存在。正如1991年的故事所显示的那样,这个国家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不仅是叛乱的少数民族,还有占多数的俄罗斯人——当时,由于经济或其他一些历史原因,俄罗斯人反叛了自己的国家。
回忆之路
俄罗斯人越来越多地询问苏联的情况,他们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和该体系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而不是它的缺点
资料来源: 勒瓦达中心,2020年
注: 被调查者被问到: “在你看来,什么最好地描述了我们国家在苏维埃制度下的历史道路?”
本文作者是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政治学名誉教授。他的最新著作《人性因素: 戈尔巴乔夫、里根、撒切尔以及冷战的终结》获得了2021年普希金图书奖。
我不接受这个问题的所有场所。多民族苏维埃国家在政治多元化条件下的脆弱性并不令人意外。真正令人惊讶的是一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甚至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认定他是一位改革者) ,竟然在理论和实际上上都支持政治多元化。在那之后,一切都结束了。
认真研究苏联的专家们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多民族的苏联国家中,有一些国家——初审、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长期以来一直渴望独立。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很明显,鼓吹分裂主义只会导致古拉格集中营甚至死刑。
戈尔巴乔夫希望把苏联团结在一起,但又有所不同。在最初低估了“国家问题”将变得多么突出之后,他试图将一个基本上正式的联邦变成一个真正的联邦国家。然而,通过实现制度的自由化并随后开始民主化,他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并将几十年的极权主义或专制统治所压抑的不满和不公正带到了政治生活的表面。
新的言论自由在1988-1989年发展成为实质性的出版自由。这使得少数民族对更大自治权的愿望得以表达。1989年3月,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西部的选民通过竞选产生了支持民族事业的议员。
但苏联联邦当局仍然垄断着克格勃(KGB)、陆军(Army)和内政部(Ministry of Internal)部队等强制手段,如果戈尔巴乔夫像他的前任一样准备好使用他所掌握的压倒性武力,分裂主义本可以立即停止。他承受着来自党国高级官员和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巨大压力,要求他采取这样的打压行动。作为苏联历史上最和平的领导人,他试图通过谈判和协议将改革后的联盟团结在一起
如果不是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要求俄罗斯从联盟中“独立”,戈尔巴乔夫可能已经成功地在他所谓的“新联邦”中保存了大多数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除了波罗的海国家)。对于一个俄罗斯领导人来说,促使一个在许多方面都是大俄罗斯的苏联解体是自相矛盾的。但叶利钦压倒一切的野心是政权和取代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位置。
可以预见的是,叶利钦的行动将导致苏联解体或联邦当局严厉打击分裂运动。如果戈尔巴乔夫拒绝使用自己掌握的强制性武力,那么他可能会被那些没有这种顾虑的人所取代。
但强硬派退出政变的时间太晚,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被软禁赶下台。那是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两个月后,因此获得了民众的合法性,使他能够反抗他们。政变策划者自己也深受戈尔巴乔夫改革带来的气氛变化的影响,与1989年邓小平在北京的做法不同,他们不准备为了恢复传统秩序而屠杀数百人。
专家观察家们意识到,在1990-91年间,各种力量朝着不同的方向拉扯,苏联解体的真实可能性。但是,哪些力量会占上风,取决于即使对主要政治行为体本身也无法预测的决定和紧急情况。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对1991年8月的政变感到惊讶(这次政变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而这正是政变的目的所在) ,而暴动主义者也没有预料到他们的接管会在几天内崩溃。因此,指望其他人预测本可能采取完全不同路线的事件的结果,是很奇怪的。

摄影: Ivan Kurtov and V. Chumakov/TASS via Getty Images